服务热线
131-1198-7613


一
我发现妈妈这个人,老是同别人想得不一样。同时,她似乎不是保存在这个地球上的人,事事自出机杼,然而又处处碰鼻。不过她从来不因此懊丧。她生气的时间,就倒在床上看书,从枕头下拽出一本《格林童话》或是《伊索寓言》什么的,看着看着,她会“扑哧”一声笑起来。我问妈妈你笑什么呀?她还笑个不绝,她说来来来,过来,妈妈给你讲个故事。她就讲《幸福的汉斯》、讲《狐狸和猫》给我听。讲完以后要是问她,妈妈你刚才为什么生气,她笑嘻嘻眨着眼睛说,哎呀刚才我是生气了吗?你看,连我都忘了那是为什么……
母亲的政治受难史
悲剧
其时妈妈学校的墙上,已经呈现了许多大字报。我知道那叫“大鸣大放”。我天天都在那些大字报底下钻来钻去,和小朋侪捉迷藏。可是妈妈很少在那些大字报下停留。她走过墙根时,步子老是急忙忙忙又魂不附体的。
天空乌云密布,一场更大的暴风雨,囊括着棍棒刃剑倾泻而下。一九五六年的“肃反”运动刚刚过去不久,反右运动又最先了。
那些日子妈妈的右眼老是跳个不绝,她觉得一场灾难又要降临了。就学校的这些先生来说,她或许可以算是唯一一个“三位一体”的“人选”了。--她身世于聚敛阶级家庭、父亲是个被判过刑的“伪镇长”;她的丈夫是个劳改刚回来不久的“历史反革命”;而她自己,历史上曾经被捕,一九五六年再次确定的审干结论上,照旧觉得她有“自首行为”,没把她打成“叛徒”,已是万幸的了。就她这样的政治状况,只要说错一个字、一句话,都将跌落万丈深渊,万劫不复。她是一只地地道道的瓦锅,且已是遍体裂纹、体无完肤。不要说有只铜锅来撞她,就是漂来另一只瓦锅,不经意地一碰,顷刻间土崩崩溃的,只能是她。
那段时间,妈妈全日里缄默沉静沉静寡言,连故事也不给我讲了。
就在“大鸣大放”最热闹那会儿,有一天妈妈垂头经过大字报前,她知道大字报的内容,大多都是反映有关常识分子报答的,好比教师的宿舍太拥挤、教学前提太粗略、学校党支部有官僚主义作风等等。妈妈当然心田赞成这些意见,但她却不愿也不敢出面露面。因此当有一天,统一个教研室的先生拦住她请她签名时,她有些迟疑不决。她明知道自己不该签名,但不签又觉得对不住同事。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潦草至极,潦草得几乎看不出是谁。
……
最先有人揭发揭发朱小玲的反党谈吐了。
所谓的“反党”谈吐,是说她曾经穿过一件银灰色的海孚绒大衣,上班时对×××说,你看这大衣照旧我完婚时,父亲送给我的,其时也不贵,如今怕是再也买不起了。
明摆着,她这不是在散布“今不如昔”,又是什么呢?
又说她熟悉一个叫刘季野的人,那人是杭一中的语文教师,一九五五年被打成“胡风分子”。她同他有过交往,应当诚实交接她和他之间的反动谈吐。
尚有人说她想让女儿学弹钢琴。带女儿去看戏,从来不看今世戏,看的都是什么外国歌剧或是莎士比亚的话剧;给女儿买的书,几乎没有几本是中国书,她这不是作育女儿走白专蹊径,又是什么?从这些毕竟可以看出,她的资产阶级脑筋何等严肃……
统一个学校的先生中,那些身世好的、那些丈夫是军人或是干部的、那些刚从师范结业的、那些历史清白的……都像是压在妈妈头上的砖块,一层层越垒越高、越砌越悬,一块块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可她却有口难辩,连表白的或许都没有,唯恐言多有失。
“瓦锅”心田大白,她必需在自己那易碎的外壳上,设法裹上一层防护的布、油毡、三合板或是此外什么,哪怕是一根稻草。她不能就此任人摆布、由人宰割。她只有自己来救自己。并且应在校带领作出最后的决定之前,反守为攻、转移目的,先把自己从火力的中间解脱出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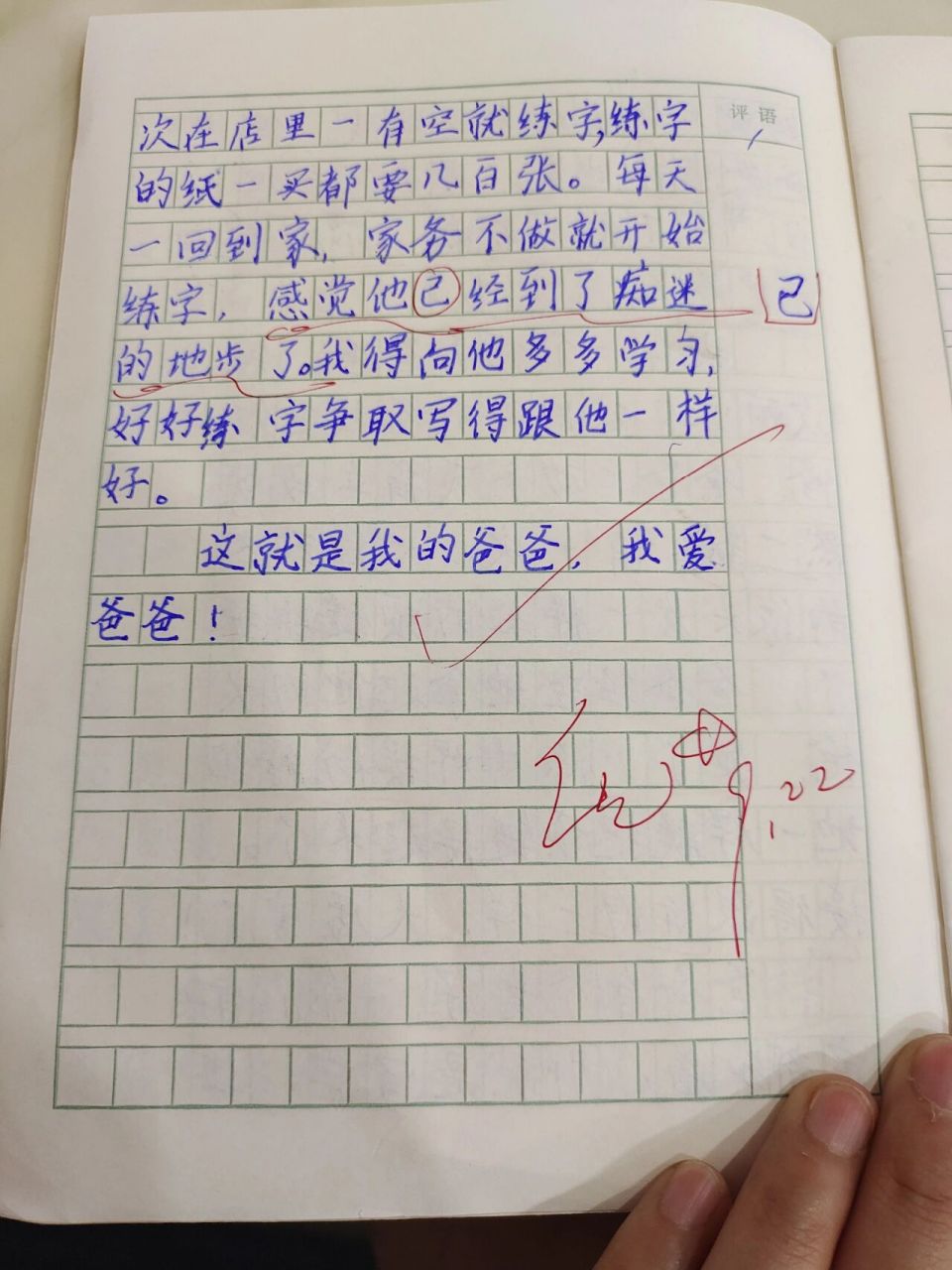
许多年以后,妈妈又一次对我陈诉了这件事。她讲得率直而沉寂,但她说她永世不能包容自己。除了贾起之死,她平生中似乎没有太多懊悔或愧疚的事情,而这却是其中的一件。
“你想那个时间,我这么一个从不关心政治、不求长进的人,还能有什么袖中神算呢?”妈妈自嘲地说,“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抛出别人、保护自己--揭发揭发此外先生。我们教研室有个女教师,传闻也有历史标题,带领把她列为重点。我就揭发她说:‘她每每在办公室,举止行为很是诡秘,写了什么器材,就搓成一团,保藏在她抽屉里的一只布袋中。这只布袋子很是可疑,它究竟有什么不行告人之处,应该将其公开在光天化日之下……’在我揭发的当天,校带领就下令她把那只袋子打开,她一边解袋口的绳,一边手都颤抖了。但成果大出意外,那里面是些废纸,尚有粉笔头、用坏了的别针等等杂物,什么格式也没有。我愣了,满脸通红。带领把那只袋子拿走了,说还要研究研究,并且表彰我借鉴性高,是好事。其时我恨不得钻到地下去。好在她后来倒没有因此而被打成右派,只是把她下放到郊区的中学去了。她临走时料理办公桌,悄悄对我说:‘你不知道,我是个基督徒,有洁癖,一点点脏器材都从来不乱扔的,就预备了那只布袋……’我这才大白了那只布袋的泉源,心田很难过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”
听完了这个故事,我同样也说不出话来。
似乎是有一点失望,对于我所恭敬的妈妈。
失望之余,又有一种伤心逐渐升起,为四面所有的人。这些年里,着实我也同样体验了这种“你死我活”的人生哲学。作为一个保存在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月的中国人,生怕几乎没有一个能幸免被人所整而又整人的悲剧。然而由妈妈亲口对我述说的这件旧事,就有了一种更为辛酸的含义。
“文革”最先后,我妈妈最后一点对于童心的依赖,也彻底破灭了。
红色的汪洋大海,红旗、红星、红袖章、红宝书、红五类……铺天盖地,无边无际。任何时间、任何所在,只要你展开眼,万物都沐浴着、浸润着红彤彤的光芒,就似乎在自己的瞳孔里面,刷上了一层红颜色。
天空也是会燃烧的吗?似乎有人放了把火。
天天太阳西沉的时间,整个城市都困绕在一种诡谲而刺目的红光之下。天空像是烧红的,湖水像是染红的,就连门前的树叶,也如涂了一层红漆。从我家的窗户那儿,能望见远远的保傲塔尖顶。晚霞中,那挺拔的塔尖,萦绕着妖艳的深紫和玫瑰红,余光灼灼逼人。
天色暗下来了。旧日的这个时间,妈妈早该回家了。
西边的残阳历久不散。利剑似的塔顶,犹如刃血的刀尖,冷冷地威震全城。血影在暮色中逐渐移动,与我们刚刚刷好的红墙遥相呼应。又逐渐暗昧为一片黑红色,隐退成夜色沉重的背景。
有一种突然袭来的可骇,紧紧攫住了我。
妈妈为什么到如今还没有回来?天天她回来的时间,老远老远,我们就能听见她踢蹋踢蹋的脚步声。
我带着妹妹到巷口的路灯下去等妈妈。望得眼睛都酸了,照旧没有妈妈的人影。妹妹说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,你听听!过了一会儿爸爸也来找我们了。爸爸轻声对我说:“你们先回去吃饭吧。吃了饭,我到妈妈学校去看看。”
吃完了饭,我对爸爸说:“照旧让我去吧!”
爸爸一九六五年从果园回到杭州后,仍然没人来打点他的“标题”。他只好在街道的构筑队当暂时工。如果他到妈妈单元去问,说不定人家还要盘问他呢。爸爸想了想,点点头说:“那也好。你可小心啊,问清晰了赶紧回来。”
我穿过长长的小巷。那条路我很熟,上小学时,我跟着妈妈整整走了五年。月亮出来了,是半个,毛绒绒地发红,像只冻僵的耳朵。
离那所中学还挺远,我就望见一股黑烟,如一条大蟒蛇,从学校的围墙上蹿起来。火光一闪一闪,像是蟒蛇的舌头一吐一伸。我从侧门那儿溜了进去,听见有嘻嘻哈哈的笑声,从操场那个偏向传过来,尚有什么器材被砸碎的乒乓声。
有一个男孩恶狠狠地喊道:“×××,你给老子出来!”又喊:“×××,你到楼上去,把老子的红宝书拿来!”
×××、×××都是先生的名字。他们不再称号先生,而是直呼其名。
我躲在一棵梧桐树反面,望见许多人围在操场上那堆火旁,正往火中一件一件地扔着锦绣的衣服。轻飘飘的丝绸在火光中飞起来,闪耀着孔雀羽毛日常壮丽的色彩。有声音喊:“这件丝绵袄不要烧了。留给老子自家穿,老子还从来没有穿过这种资产阶级的丝绵袄哩!”又是一声巨响,一只半人高的青花瓷瓶从楼上扔下来,在操场的石台上摔得粉碎,碎片崩在我的脚边。一个苍老而嘶哑的声音号啕大哭,含糊不清的哭声似乎在诉说着这只花瓶的泉源。
“打垮大叛徒朱小玲!”
“朱小玲不克服敬佩,就叫她殒命!”
妈妈走过贴满口号的走廊,被几个弟子推进了礼堂侧面的扮装室。门重重地关上了,身后传来铁锁的咔嗒声。她在黑暗中闭了一会儿眼睛,才勉强看清小屋里空空荡荡,连一把椅子都没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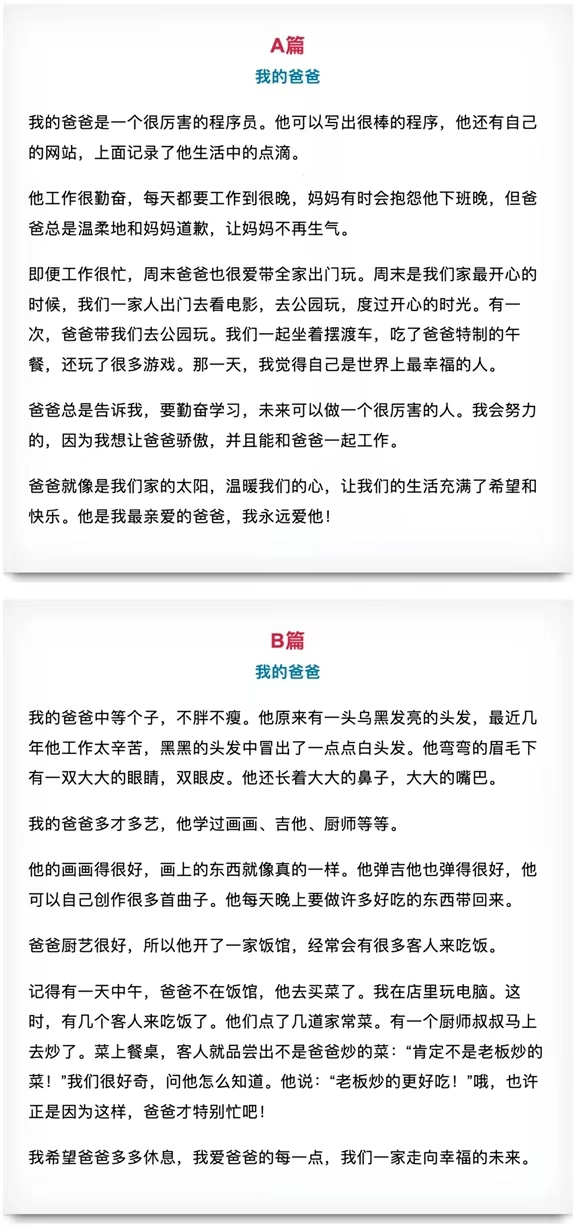
整整一夜,妈妈坐在扮装室酷寒的台阶上,一分钟也没有合眼。
附近是冰冷的墙壁。没有天空也没有窗户。死日常的静寂中,只有自己单薄的呼吸,犹如一个遥远的回声,在云雾中飘浮……
伸出手去,一摸一手灰。尘土蓬松而厚实,像一只垫子。
有什么器材轻轻地蜇了她一下。她的手指掐到一个黏糊糊的小虫子。接着她闻到了一股异味,奇臭无比。
……墙壁、尘土、臭虫和黑暗……令人窒息。暗昧中她觉得这个处所似曾了解,她能闻出来--失去自由的牢笼,连室内的气息都是一样的。
她这平生中,已在这种处所待过许多次了。第一次是在天目山的国民党牢狱,为了她填过表申请到场共产党;第二次是解放初,在茅家埠都家花园,为了查看她蹲过国民党牢狱的历史。第一次死了贾起;第二次,死了直属班里她熟悉和不熟悉的那些人--是否可以表白说:死人的事老是经常发生的。这就是理想的价格?
但这第三次呢?既非政府也非机关更非司法部门,而是一种闻所未闻的“革命群众专政”,迅雷不及掩耳,派头汹汹,横暴而疯狂。在她四面的人中,已有一个又一个的人投水、服毒,以死来证实自己的清白……那么这一次,是否该轮到她了呢?
那一夜,我的妈妈久久地独坐于阴湿的水泥地上,一动不动,几近麻木。那个关于死的念头在她脑中一次次闪现。她想着解脱自己平生魔难的时辰终于降临,以致感到了一阵轻松和如意。晨光已透过门缝,泻在她的脚边。地上的尘土逐渐变得苍白,在朦胧的天光中,像是一片积雪的屋顶。当太阳出来时,它们就将一滴滴化为乌有……
那一夜,爸爸坐在家里的灯下,一夜未眠,一言不发。凌晨时我被一阵剧烈的头痛搅醒,我喊着妈妈惊坐而起,那个瞬间我脑中闪过学校里那个跳楼的女教师。我必定在那个时辰妈妈必定也曾有了这样的念头,我在床上缩成一团,心田充满了惊愕。
第二天,妈妈被红卫兵们从扮装室移到楼梯底下堆放杂物的一间小黑屋里。只有用饭时,才承诺出来“放风”。十几个被关押的先生,排成一行,集体押去食堂。划定不许买一毛钱以上的菜,也不许端回屋里去吃,而是在食堂门口站成一排,作吃饭表演。午时我去给妈妈送被褥和更换的衣物时,远远地望见那些“牛鬼蛇神”们,正排列在食堂外貌,大声朗诵着一段最高指示:“凡是错误的脑筋,凡是毒草,凡是牛鬼蛇神,都应该进行褒贬,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……”我朝妈妈走去,但“小将”们一把将我手里的器材抢去了,却不让我见妈妈。
这样关押了一段日子,除了写材料和“提审”,那个头发黄黄的、绰号叫“黄头毛”的红卫兵,下令这些先生最先劳动改造。有一次粉刷礼堂的墙壁,墙很高,要站在一张桌子上、再站在一张凳子上才气够得着。妈妈很艰苦地爬上去,没想到桌子腿是瘸的,人一站上去,身子一晃,连凳子一路摔下来,跌得鼻青脸肿,申请到校医务室去上点红药水,也被红卫兵断然拒绝。持续许多天,妈妈踮着脚尖,走路一拐一拐,疼痛钻心,大汗淋漓,头发都湿透了。
过了些天,她又被下令到拱宸桥去拉煤、拉砖、拉石头。一个人拉一车,天不亮就出发,拉着空车走去,直到天黑,才气筋疲力尽地把满满一车石头拉回来。妈妈最怕过那座大关桥,桥身又高又陡,拼了命把车拉上桥,已是头晕目眩;到了下桥时,一车重载,板车往桥下死命地冲下去,她八十多斤的体重,底子就压不住车身。有一次,车子下滑时,车头却翘了起来,她被吊在车把上,整个人都已悬空,眼看就要翻车,她惊叫,脑中已是一片空白。好在有几个老工人听见冲过来,用力按住车把,才算是救了她一命。她面色苍白地瘫在地上,想说声“谢谢”,喉咙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再走,发现鞋子已经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只好趿着,一步一趔。如果全国上真的有水晶鞋呢?她想。不过照旧不要什么王子了吧,只要穿上了那双水晶鞋,酿成了旋转一天都不觉累的人,就好了。她想着,脚上竟逐渐有了力气。
到校外干活究竟能有阳光和希奇空气。她老是安慰着自己。
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,又是没完没了地写材料。写完了交上去,好多天也没人理睬。她发现着实红卫兵对他们写的材料并无多大爱好,他们最热衷的是拿到材料,然后轮替出去“外调”,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。妈妈一个人被单独关在楼梯下那间小黑屋里,小屋子本来是有一扇窗户的,但窗户外貌贴满了大字报,把窗缝糊得密不通风。门一关,屋子里黑得像座墓穴。一个十五瓦的电灯泡,便是她保存中唯一的光明。有一天,她突发奇想,用一根头发上的发卡,插到窗缝里,把窗外貌的大字报一点一点捅破,再逐渐地挑出一条裂缝。大字报一层压一层,糊得又厚又硬,她觉得自己差不多是在挖掘一条地道,手指都磨出了血。捅开这条只有一根发卡那么细、筷子那么长的裂缝,泯灭了她整整好几个晚上。
一九六八年纪末的最后几天,下了一场大雪。妈妈的隔离查看依然遥遥无期,看不出一点儿松动的迹象。那个严寒的冬夜,城市大街小巷的上空,传扬着一个震撼全国的声音,收音机里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庞大领袖的最新指示:“常识青年到农村去……”我和爸爸面临面坐在桌旁,听完了最新指示,谁也没有语言。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学校。那天傍晚回到家,坐下来吃晚饭的时间,我对爸爸说:“反正,上山下乡是迟早的事情,晚去不如早去。我想……”
“你想什么?”爸爸的眼睛盯住我问,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下。
“我想……我想报名到黑龙江去……同砚说,有黑龙江成立兵团和农场的名额,是发工资的……”
我知道说出这个决定须要勇气。我不是要去浙江农村,而是去中国地图上最顶端的北大荒。我说得结结巴巴很吃力,因为我的眼前不单坐着爸爸,尚有爸爸所代表的妈妈。妈妈尚被关在牛棚,“黑龙江”这三个字对于妈妈来说,意味着一次生死未卜的持久星散。
“不行!在你妈妈回来之前,你哪儿也不能去!”爸爸斩钉截铁地中兴我,扔下碗就走了开去。
自从一九六七年妈妈被隔离查看以后,不断到一九六九年六月我终于去了北大荒,在这一年多妈妈不在家的时间里,这个家,暂时是由我主持的。
学校里停课闹革命,后又复课闹革命。但革命着实没我们什么事。“一月风暴”刮过了,革委会创建了,牛鬼蛇神都专政了,工宣队也进驻了。我们这些“清早七八点钟的太阳”,在学校里议论的,都是上山下乡这个话题。
如果我走了,爸爸和妹妹怎么办呢?
我走向那么遥远的北方,我什么时间才气再会到妈妈呢?
我在校园的小树林里持久伫立,紧紧咬着嘴唇,望着远处人声鼎沸的北大荒农场的报名站。
北大荒--一个何等遥远的处所。然而,“遥远”却是一个解脱眼前禁止的唯一通道;是一个若隐若现的渴望和等候;草绿色的棉大衣和绑腿,更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。当那个月夜我在小巷里疾驰的时间,或许作乱就早已被注定了,就像妈妈的十九岁。十九岁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纪。十九年中妈妈的脐带始终犹如救生圈绕着我的脖颈,输送给我天际的海市蜃楼和岸边的泡沫。然而作乱的迹象着实早就隐约明示,“文革”只不过是使我终于下定了决心,去咬断自己同脐带最后的那个连接点,见义勇为。
更况且,用妈妈自己的话说,她的查看是一场“持久战”啊。我等候这“战争”的结束,要等多久?
我的去意已决,锐不行当。在我和爸爸发生了多次剧烈的辩说之后,他知道已不或许阻挡我,便不再理睬我。我想他不会设法告诉妈妈,因为那只会让妈妈加倍痛楚。于是我销户口、办手续、料理行李,一切预备工作进行得机密而又坚决,连我自己都感到诧异。街上从早到晚传来一阵阵眉飞色舞的锣鼓声,一辆辆卡车载着一群又一群胸口佩戴红花的知青,奔向辽阔天地。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,震耳欲聋……同这一切热火朝天的环境比拟,妈妈显得何等渺小、何等懦弱、何等不重要啊。妈妈像一片秋天的落叶,从我心上无声地飘逝。
我决定瞒着妈妈。不断瞒到我上了火车。我还决定不去同她辞别。我怕望见了妈妈,心田一难受,万一就摇动了呢?
临走的前一天,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,急忙写道:
“亲爱的妈妈,庞大领袖教导我们,一个有前程的文学家,应该到火热的保存中去,和工农群众相团结。你也曾不断这样对我说。
“如今我就要到真正辽阔的北大荒去了。你要信任党、信任群众,多多保重。”
我转过身,凶神恶煞地对妹妹下令道:“等我走了,你再把这张纸条交给妈妈。”并叫她不要哭,我会来信的。
吃过晚饭我就脱离了家。为了早起,那晚我住在了同砚家里。那是一个初夏的朝晨,阳光辉煌光耀,红旗飘飘。火车站人头攒动,人山人海。我意气风发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,坚定无畏的脸上没有一滴眼泪。车轮逐渐脱离月台的时间,我的眼前突然闪过一张悲怆而惆怅的面孔,她从千万万万的生疏人中解脱出来,扑向车厢,温柔地低声召唤着我的名字。那个时辰突然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,疼痛撕裂着我的五脏六腑,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惊。揉揉眼睛,眼前却只有上上下下一片草绿色的军装晃动。我转过脸去,城市里破旧的房屋和街道逐渐退出了视线,当面吹来了遥远的北方刚劲的春风……
然而我信任感应。我大白头痛是一种征兆。不久后我接到一个同砚的来信,证实了我的猜测--就在我快走的那几天里,爸爸终究觉得这样巨大的事情不能不让妈妈知道,他照旧叫妹妹设法把我走的新闻告诉了妈妈。爸爸渴望妈妈能向工宣队请假,承诺她回来同女儿见上一面。但工宣队拒绝了妈妈的请求。
那天后三更,妈妈终于不顾一切地弄开了隔离室门上的锁,手里拿了一把扫帚,偷偷推开了学校虚掩的大门,想溜回家送我。她把扫帚放在大门边上,渴望自己天亮以前能赶回来,万一让红卫兵发现,也可说是扫地,有个借口。可等她到家时,我早已离去,妈妈呆呆地望着我空了的床铺,顿时傻了一样。哭亦无泪,更不敢在家中久留,急忙赶回学校去。天已微明。却偏偏就在校门口被专案组出来上茅厕的人撞上。为此,全校又召开了一次声势浩荡的褒贬会,褒贬她畏罪潜逃,妄图翻案,匹敌运动。妈妈在台上弯腰九十度,足足站了四个小时。褒贬会结束时,她已不会走路,腰椎间盘脱出,大病一场。那年她四十五岁。
我知道自己罪孽深重。这是我平生中唯一对不起妈妈的一段旧事。十九年来我同她相依为命,但我却在她最须要我的时间不辞而别。其时,妈妈历尽魔难的生命,已如游丝奄奄系于千钧。我的远行,在她不堪重负的劳顿和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中,犹如雪上加霜。她的痛楚不在于我下决心去边疆,而在于我恰恰是在她身陷囹圄时离她而去。要是没有爸爸和妹妹,她怎么尚有勇气活下去?这是我平生中永世无法解脱的愧疚和自责--当我离家北上时,我怎么竟然会如此绝情又如此冷淡?革命的大水,毫不艰苦地就把妈妈十九年里一口一口喂给我的温情、道义和童心,彻底地摧毁殆尽。我已不是妈妈的孩子了。
然而许多年以后,妈妈沉寂地同我谈起一九六九年的那次“作乱”。出乎我们大家的猜想,她却有与我和爸爸完全不同的见解。她说我十九岁那年选择了北大荒是一个生命的必定--既然遥远的森林和雪原曾是年青的妈妈梦中的召唤;当我尚在妈妈腹中时,她已将憧憬飞雪与冰凌的基因植入了我的体内。所以安知北大荒不是一种理想的成果呢?或许我那次毅然决然的办法,恰恰就是她自己那种与生俱来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持续?在她女儿身上亦无法改变。
至此,妈妈在她对世事万物的宽宥中,完成了她对自己的阐释。
但人生仍然不能没有梦。没有梦的人生,日间太苍白,黑夜太漫长。正是因着噩梦终究会醒,而美梦总也不能成真,人类才周而复始地轮回着,轮回着人类实现理想的那个痛楚的轨迹。
妈妈和她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人一样,亲手炮制了那个锦绣的梦。她的平生始终被梦魇所纠缠,她的渴望湮灭在自己的梦里。
她是那个梦的成果。但她恰恰也是那个梦的缘故因由。
—
—
莫言:这年照旧要过下去
教育 ?? 恨"拼爹"、忙移民,都不如父母坚持终生进修和成长
?經典英語情歌? Have I Told You Lately That I Love You 獻給 爱人 最美的歌
你为何默认这样的教育?我们孩子的童年,尚有他们的青春,全都被考试绑架!
参观真的可以改变你?
—
—

2024-03-20
网页设计,是根据企业希望向浏览者传递的信息(包括产品、服务、理念、文化),进行网站功能策划,然后进行···

2024-03-19
网页设计,是根据企业希望向浏览者传递的信息(包括产品、服务、理念、文化),进行网站功能策划,然后进行···

2024-03-19
网页设计,是根据企业希望向浏览者传递的信息(包括产品、服务、理念、文化),进行网站功能策划,然后进行···

2024-03-19
网页设计,是根据企业希望向浏览者传递的信息(包括产品、服务、理念、文化),进行网站功能策划,然后进行···